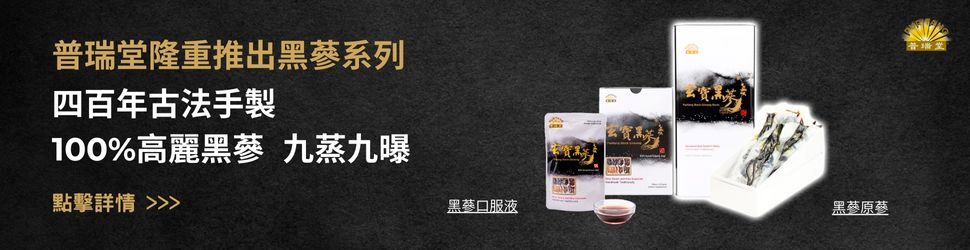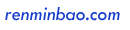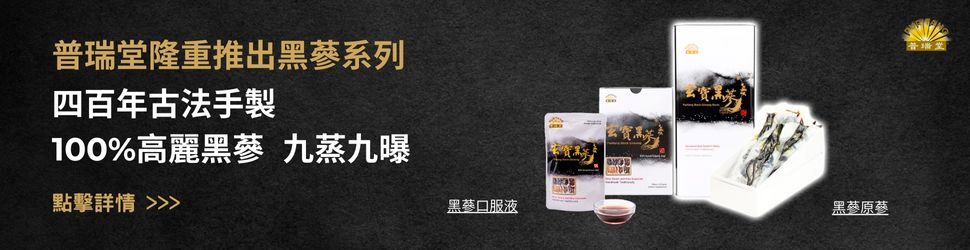|
|
 |
 |
 |
|
2025年8月27日
發表
人氣:42,187
分享:








|
|
|
| 觸目驚心 毛時代知識分子自殺檔案之文革篇(三) |
| |
|
謝泳
|
|
【人民報消息】在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出現的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的現象。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於了解毛時代給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這一時期其它階層的生活狀況。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裡,突然出現異常的知識分子自殺高峰,這個現象從反面證明,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不僅具有摧毀社會傳統的能力,而且對知識分子懷有特殊的敵意。本文摘自愛思想,作者謝泳,原題為《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
自殺是一個常態社會中始終存在的現象,本身並不足為奇。之所以考察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情況,是因為這一期間此類人士的自殺人數驚人。一個社會突然出現大量的自殺現象,特別是知識分子自殺,顯然是不正常的。這種自殺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正常社會裡常見的自殺原因不同。因此,本文不會從社會學觀察通常的自殺現象的視角來分析上述情況,而是通過剖析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來研究這一現象的發生。
本文選擇的研究時段為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上這一時代可以被稱為毛澤東時代。文中涉及的主要案例起自1950年,截止於毛時代結束之時。由於中國大陸有關的檔案尚未解密,所以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檔案檢索而統計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自殺的完整人數(在檔案開放的情況下這並不難做到)。本文只能根據有關的回憶和有限的訪談及調查,選取一部份知識分子的自殺情況作為研究的基本材料。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材料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一,當事人的回憶錄和相關的回憶文章;二,筆者對死者家庭的訪問記錄及朋友提供的材料;三,《內部參考》,此刊物為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輯的內部參考資料,1949年9月22日創刊,每日一期,供主要官員了解國內國際動態,本文注釋均注明引文出處之期號和頁碼。需要說明的是,1949年至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多數人並不知名,但由於相關資料極難收集,所以本文據以分析的知識分子自殺資料偏重於知名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學者、名演員、科學家、大學生等。
一、不同時期的的自殺現象
3. 「文革」期間
「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像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最高峰,反右後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運動而導致大量自殺的現象又開始集中出現。僅湖南省道縣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間被迫自殺的即達326人;文革期間,零陵地區的自殺人數達到1,397人
在文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據那裡的教師敘述,當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現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筆者曾看過的一個材料說,僅在北京大學,「文革」初期和工宣隊進駐期間,自殺的著名教授就有24名。 北大歷史系共青團總支書記、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的吳偉能文革中曾經是「左派」,擔任了歷史系文革委員會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他悄悄離開了「學習班」,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死後第二天,北大歷史系召開了針對他的批判會,給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在吳偉能的屍體被發現時,圓明園的那個池塘裡還有三具屍體,其中有一對夫婦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老師。
其實,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國,豈止是北大一校。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清史專家、副系主任傅洛煥看到大字報和遭到「鬥爭會」攻擊後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殺。文革時天津有一陣子自殺成了風,據說是由市委書記萬曉塘、副書記王亢之的自殺開的頭。一位天津的老大夫告訴筆者其親自目睹之事:1966年8、9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他在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上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會見到兩、三具。由於人們普遍見過投水自殺的屍體,以致於北京市民中流傳著一種說法,不用看死者的面容,僅看屍體浮起時的狀態就知道死者的性別,女的仰著,男的趴著。這種生活經驗大概是中國人獨有的。
「文革」中自殺現象與以往不同的一個特點是,隨著政治運動向社會各階層全面延伸,其殘酷程度越來越高,自殺行為也蔓延到了社會各階層,不再集中於某幾個階層。從大學到中央機關,從普通工人到中小學生,都有人遭到或懼於政治迫害而自殺。但迄今為止關於這一時期自殺的記錄始終是零散的。 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怪的特點,即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筆者居住的大院裡「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文革中的自殺行為一直延續了幾年,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材料,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即達一萬多人。由於關於文革的資料和回憶錄比較多,讀者可以從許多出版物中找到類似敘述,這裡就不再進一步說明了。
二、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分析與評價
在已收集到的1949至1976年間自殺者的案例中,以知識分子的自殺最引人注意。下面的分析以筆者選擇的部份知名知識分子的案例為基礎,這一名單與上一節注[21]的自殺名單基本不重覆。在這一名單中的知識分子多數是本世紀上半葉的大學畢業生,不少人曾留學國外,多半學有專攻,是各自學科或領域內的骨幹,也可以說是民族的知識精英。他們在中共建立政權時都留在大陸或在中共建政後特地從海外回國,投身祖國的科學文化建設事業。他們是愛國的,並非中共的政敵,不少人甚至就是中共早年的黨員和重要幹部。但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這樣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政治打擊的對象,使得他們走上了絕路。
1. 39例自殺案例的歸類分析
為找出自殺現象的共性特徵以研究其成因,筆者曾按下列項目分析對比過名單中的案例資料:1.自殺的具體時間和地點。2.自殺的具體方式(如跳河、跳樓、跳煙囪、跳海、跳井、跳糞坑;自縊;打開煤氣;服過量安眠藥;觸電;切斷動脈;臥軌等)。3.自殺的直接動機。4.生前工作單位。5.生前經濟狀況(主要指收入)。6.自殺前的身體狀況(是否患有疾病)。7.自殺時的婚姻狀況(主要指是否與配偶不和)。8.自殺時與子女的關係。9.自殺時的年齡。10.自殺後單位的結論。11.自殺者家族成員中有無自殺史。12.其他特殊情況。
經過歸納分析後,發現了如下特徵:
第一,在諸種自殺方式中死者通常選用最簡單、成功率較高的方式,如跳樓、自縊,這表明知識分子自殺時的絕望程度和必死的決心。他們選擇的自殺方式還受制於物質條件的制約。例如,只有少數人選擇打開煤氣的方式,且集中在家庭煤氣使用率較高的上海;自殺的高級官員中多採用服安眠藥的方式;而其他自殺者則往往選擇自縊和跳樓等痛苦或慘烈的方式。
第二,自殺者中,除少數人外(老舍67歲、饒毓泰77歲、盧作孚69歲、王重民73歲、周瘦鵑67歲),其餘35人的年齡約在45歲至55歲之間。自殺者的這一年齡特徵說明,自殺的知識分子中以年富力強、正處在事業高峰期的中年人為主。例如,其中有張宗燧、饒毓泰,謝家榮、湯非凡四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饒、謝兩位還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還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國學大師。這個年齡段的人一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既然處於這一年齡段的知識分子有較多自殺者,說明社會生活是極不正常的,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絕路上,一般情況下其自殺動機本來可能會比其他年齡段的人低。
第三,自殺者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作協文聯、藝術團體,這些職業恰恰是「思想改造運動」、「反右」和「文革」的矛頭所向。
第四,自殺者中有不少是夫妻雙方同時自殺,如翦伯讚夫婦、傅雷夫婦、吳晗夫婦、聞捷夫婦、劉盼遂夫婦、劉綬鬆夫婦、楊嘉仁夫婦、田保生夫婦、李紱夫婦、張宗穎夫婦。這種現象說明,這些自殺者的婚姻狀況良好,他們選擇這種方式反映了夫妻雙方對自殺身死有高度認同。
第五,絕大多數自殺者的家族中都沒有自殺記錄,從自殺者的性格、年齡、經濟、婚姻狀況裡,都找不到明顯的自殺理由。由此可以推測,這些自殺現象的原因與社會學通常對常態社會裡自殺現象的假設不同。
2. 自殺現象的原因解析
著名社會學家愛米爾·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曾對自殺現象做過系統的研究,他從對宗教活動、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體的研究中,將自殺的類型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利己型(egoistic),這類自殺的根源在於個人未與社會融為一體;第二種為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即自殺者出於高尚的信念,如為宗教信仰或義無反顧的政治忠誠而貢獻自己的生命;第三種為動亂型自殺(anomic),它的產生是由於個人缺乏社會約束的調節,個人需求和慾望的實現受到了社會的制約。杜爾凱姆將自殺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因素的思路,給人們很大的啟發。他認為,自殺與社會環境有關;正是從自殺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才能找到某人自殺的根源和背景。
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狀況,恰好能從它們發生的社會環境中找出根源。但是,導致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的原因與杜爾凱姆的分析並不吻合。因為,杜爾凱姆所描述的是常態社會中自殺現象的一般規律,而筆者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卻是一個非常態社會中知識分子自殺的奇異現象。杜爾凱姆有關自殺的理論難以解釋中國的這種自殺現象。僅在分析某些個案時,杜氏的理論或許有參考價值。
在1949年至1976年間自殺的大批著名知識分子與他們所處的社會之間,本來並不存在特別的緊張和衝突,但是,在當局有意識地引導操縱下,形成了一種對知識分子強加政治壓力的社會政治環境,這種壓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達到了高峰,而知識分子的自殺率則與這幾年政治運動中的政治壓力高低完全成正比例。在已知案例中,自殺的時間集中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這三次高峰,這些自殺高峰與當時的三次幾次政治運動的高潮期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這些政治運動的實質。
這一時期出現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還帶有明顯的突發性和傳染性。當許多人處於幾乎相同的政治壓力之下時,個別自殺者的行為具有對其他社會成員的某種暗示性,而別的正感到恐懼的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這一暗示,而選擇相同的結局。例如,1966年9月3日著名音樂家傅雷夫婦自殺後,僅過了三天,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殺;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該音樂學院鋼琴系系主任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隨後,該院的音樂理論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陳又新也相繼自殺。
在這二十多年裡,有這麼多的知識分子選擇自殺的道路,確實是令人吃驚的。從這些案例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自殺的原因。
首先,這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制度產生了一種嚴重威脅知識分子生存的氣氛。在自殺者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義理想、並有留學和國外生活背景的知識分子為多。這些知識分子曾經感受過自由社會的生活方式,他們回國前或者對中共的制度不了解,或者是對這一制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結果國內現實的政治環境與他們所期待和願意接受的顯現出巨大的差異。發現受騙上當後,他們的內心可能長期處於複雜的矛盾狀態下而無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臨的政治打擊,就很可能導致他們的精神崩潰。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當年從香港回到中國的三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姜永寧、容國團和傅其芳,最後全都選擇了自殺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識分子本來是可以選擇離開中國大陸的,由於對新政權抱有幻想而留了下來。當後來他們面臨政治高壓時,或許會對自己當年的選擇有一種追悔莫及之感,這也是令他們走上自殺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次,五十年代初期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產生了一種媚上賣友、不擇手段打擊同事甚至親友的極為惡劣的政治文化,而且這種政治文化被冠上「革命」的旗號而受到政府鼓勵。社會當中充滿了對立,中國社會中傳統的友情被無條件對黨和幹部的效忠所替代,正常的社會人際關係受到很大的破壞。這樣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也是這些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從以往早已習慣了的比較自由的社會環境落入這樣惡劣的社會環境,並且毫無選擇地不得不在其中生存下去,使許多知識分子的身心受到摧殘,個人與社會的緊張關係無法通過任何渠道釋放出來。人際關係的普遍惡化,甚至使家庭、親戚、甚至長幼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異化。知識分子自守的個人道德和人格,無法對抗這種由政權強加給整個社會的無道德化,因而他們會有孤立無援之感。長期生活在這樣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氣氛中,讓許多正直而潔身自好的知識分子產生厭世的社會心理,這是自殺現象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
再次,五十年代以降,社會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日益取代、甚至消滅了傳統的日常文化生活;人為地製造階級對立,使整個社會普遍缺少人道主義精神;由於取消了教會,使一切與教會相關的博愛觀念都淡化了。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人都自顧不暇,甚至人人自危,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社會成員也普遍失去了人類本應有的同情心。在這種情況下,絕望而有可能走上絕路的人們以及已經自殺的死者,不但得不到別人的關心和愛護,反而受到更嚴酷的打擊。從本文列舉的自殺案例中可以發現,某人自殺後,其所在單位往往不會放棄對他們的批判,他們的多數在「畏罪自殺的」名義下而被罪加一等。巴金曾說過:「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功擊死者。」不僅在社會基層如此,黨政高層也毫不關心絕望者的命運。毛澤東就曾對他的醫生李志綏說過這樣輕鬆的話:「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對自殺現象缺少起碼的人道關懷,也是加劇自殺現象激增的原因。
第四,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自殺率,與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間政治運動中對他們人格的惡意侮辱有關。從已知的自殺案例中發現,自殺者往往相對地集中在這樣幾個社會群體,即大學教授(學者)、作家、大學生、名演員。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和日本,作家自殺的情況比較為人熟知,而歷史上中國作家卻很少自殺。為什麼在特定歷史時期在這些知識分子中卻集中出現了一個自殺的高峰呢?其原因只能從那一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從案例中發現,當時對知識分子的人格污辱有時甚至超過了政治迫害。比如,當年武漢大學教授劉綬鬆夫婦就是在被人當面扇了耳光之後自殺的,其他諸如老舍、傅雷、翦伯讚等都有類似情況。知識分子是高度自尊傳統上也受到社會充份尊重的社會群體,只是到了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才史無前例地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有系統、刻意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這是許多知識分子自殺的直接原因。
最後,自中共建政以來,除了連續不斷的政治高壓外,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也迅速縮小,他們一旦受到打壓就只有死路一條。知識分子以傳播思想文化為職業,但1949年後完全取消了新聞和出版自由,逼著知識分子只能依賴現存體制生存。同時,政府壟斷了幾乎一切知識分子可能就業的場所。如果知識分子被這個體制所排斥,他們將再也無法以自己的知識技能謀生,而只能去從事體力勞動;而對一些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來說,失去了原來的職業,他們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數知識分子受迫害後的絕望正是由此而生的。這種為了明確的政治目而塑造的嚴酷的生存環境,是導致這一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現象急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這一時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既不同於帝俄時代的流放,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謫貶。在那樣的時代裡,在皇權之外還有民間社會,被正統貶斥並不意味著在民間無法生存。而在1949年至1976年間,民間社會基本上消失了,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後根本就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當時對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處理方式通常是兩種,一種是將其下放到最為貧困的地區,另一種是將其遣返回鄉。兩種方式都以急劇改變知識分子的生存條件為特點,從肉體和物質上進行雙重折磨。前一種方式把原來生活狀況尚屬中上的知識分子(其中許多習慣於南方氣候)送到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等地最偏僻的鄉間,故意從物質條件和精神狀態兩方面長期折磨他們,目的是要讓思想上比較獨立的知識分子臣服。後一種方式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則是雙重的,中國有榮歸故里、衣錦還鄉的文化傳統,但把來自農村的、好不容易才從鄉間掙扎出去的讀書人遣返回老家,讓他們戴著右派、歷史反革命、特嫌、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在故鄉的前輩、親戚、朋友面前認罪,是對他們的尊嚴的最後的嚴酷打擊。在1949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裡,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打擊方式已經成為一種受到主政者鼓勵的政治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裡,這無形中對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時考慮最終出路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
三、結論
在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出現的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的現象是人類的恥辱。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於了解毛時代給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這一時期其他階層的生活狀況。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裡,突然出現異常的知識分子自殺高峰,這個現象從反面證明,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不僅具有摧毀社會傳統的能力,而且對知識分子懷有特殊的敵意。本文所研究的自殺現象對中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極為明顯的,而且為禍之久,至今仍未消失。知識分子的大批自殺與打擊知識精英的其他結果一起,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科學技術和人文藝術的正常發展,造成了學術文化發展的斷層,進而妨礙了現代化的進程。這些損失可能是永遠也補不回來的了,何況這一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束縛著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由此就更可以體會到堅持類似研究的意義。
來源:民主中國
△
|
| 文章網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5/8/27/92055b.html |
|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
|
|
|
|
|
 |
 |
 |
|

|